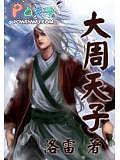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男人只会影响我搞钱的速度 > 第九十九章 回乡(第2页)
第九十九章 回乡(第2页)
沈照早就备好了年货,让来县里拖油渣的顾天朗带了回去。定县人冬天有熏肉做腊肠的习惯,可上桥村里人前几年连饱肚子都难自然没有多的肉能拿出熏。这两年就算是好些了,买点肉能把年糊弄过去也就差不多了。
唯独今年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赚到钱,家里喂的猪从下半年开始食里添了油籽饼,个个养得膘肥体壮。别说小孩子看着眼馋,就是大人也动了心思。也不知道是谁家起的头,杀猪的时候少则留十斤,多的存半扇。到供销社买那专用的粗盐粒,路上遇上别村的人问,扬着声音喊:“啊,买盐回去腌点腊肉给孩子们尝尝味。”
别村的人听得真咋舌,这十里八村大家都是穷在一处的。怎么偏偏就这个上桥村,眼看着就要不一样了?
沈照的记忆里千禧年以后,家家户户腌腊肉灌香肠是老传统。重生回来完全没听阿妈说起,等她起了话头时间都过了。
沈周氏陷入了回忆,“我长这么大还是嫁人那年吃过一口老腊肉,这村里家家户户能混到肚饱都了不起了,哪还有钱腌腊肉?你要实在想吃肉,卤了也是一样的。”
沈周氏这几个月的生意做下来,卤肉的方子改进了不少。纺织厂那一片本来还有三五个人和她抢生意,可最近这两个月都老老实实换了地方。
沈周氏现在会赚钱,家里伙食上也舍得。家里荤腥没断过,有时候要是有牛羊还会顺手买两斤给外孙女解解馋。
小家伙因为差点被抱走的事,有段时间没去托儿所天天跟在外婆屁股后面转。她不淘气,还聪明。沈照又舍得在女儿身上下功夫,走出去真跟菩萨面前的小金童差不多。来买卤味的人总爱逗她。可不管人家怎么逗她都不哭,反倒有时候蹦出两句金句惹人哭笑不得。街坊四邻都说沈周氏有福气,养出这么可爱的小仙女。
在城里呆久了沈周氏发现这世上家里没儿子的好像也不止她家这一户,但大家好像都活得还不错。特别是这些年计划生育收紧,只生一个女儿的大有人在。人家照样和和美美,日子过得不比别人差到哪里去。
沈周氏不懂,但小丫头在身边待久了。祖孙两个的感情倒是一进千里,就连今天回村都是沈周氏把人紧紧地护在怀里。
顾天朗今天是专门来接沈家人的,这年头回村里除了自行车就是两条腿,公交不来这种穷乡僻壤,私家车更是想都别想。
祖孙三个穿得再暖和也被寒风吹得够呛,可刚进村就觉得再冷也受得。
古人都说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
沈周氏自从再次开摊做生意就没停过,自然也没过上桥村。虽然她知道女儿同村里做了买卖,但不知道这买卖做得这么值得。
拖拉机刚到村口,村头老张头从地里回来背篓里的萝卜就非要塞给沈家母女。
沈周氏自然不肯要,谁不知道老张头就是一个寡人,家里无儿无女平日只有别人给送他的,哪有吃他的道理。
老头也倔,“咋滴,是看不上我这几个水萝卜是不是?”
“张老汉,你这是说啥话。阿照回来没去看你都算了,怎么还能要你的东西。”
“咋不能要?”老张头红着眼睛看向拖拉机的小娃娃:“咱地里的萝卜,水头足。给孩子炖着吃滋补。我送不起肉,添点配菜都不行了?”
话都说到这份了,沈照干脆做主收下了。
老人见状,抹了把眼泪摆摆手往家里走去了。
“咋滴啦?这是?”沈周氏也是猜不出这人无缘无故的哭什么?这莫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顾天朗坐在驾驶座听了半晌,自然是知道原因的。
“咱上次那笔生意村里分了不少钱,除了拿了些出来补砖窑,还给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六岁以下的孩子每人发了五块钱。像老张头这种孤寡老人再多发十块钱,十斤米,五斤油,五斤肉。虽然不多,但大家应该能过个热和年。”
沈周氏听得直咂舌,这种事别说是老张头了就是她自己都想都不敢想。想到这些钱都是女儿带着大家伙赚的,不知怎么的心里头暖烘烘的。